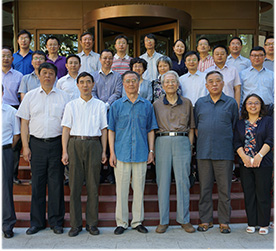[内容摘要]: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所持有的观念形态继承了宗教(基督教)以抽象的精神观念能动地把握世界的方式,从而都具有了唯灵论特征。因而,马克思把对宗教唯灵论的批判看作是政治与经济领域批判的前提。在政治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把私有财产制度抽象人格化,从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来论证自由和平等,从而使建立在这种抽象人格基础上的自由和平等等政治国家的政治理念日益抽象化,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的头脑且企图实现所谓的普遍利益而具有唯灵论特征;在经济领域中,资本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最高峰,资本这一抽象的“死劳动”借助于雇佣劳动这一“活劳动”得以不断增殖从而具有了支配人的灵性。马克思对这三种唯灵论批判的意图在于提醒人们要搞清楚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形态和观念形态之间的差别,不被抽象观念所支配,从而唤醒工人阶级的彻底的革命意识。
[关键词]:马克思;宗教唯灵论;政治唯灵论;资本拜物教
通常来讲,唯灵论首先是一种主张灵魂或抽象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或主宰的宗教世界观。基督教通过对上帝的崇拜使得上帝的神圣精神对悔改赦罪的人进行控制,从而具有了唯灵论的特征。以反宗教蒙昧并高扬人的主体性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哲学强调“必须要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语)”[1],这样一来,结果就是黑格尔所指出的:“鼓舞着、激励着人的,是内在的、自己的精神,而不再是功德”,“教会就失去了支配精神的权力,因为精神本身已经包含着教会的原则,不再有所欠缺了”[2]。但事实上,启蒙运动哲学对基督教的批判实际上又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即对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崇拜。用卡尔·贝克尔的话来讲就是:“对人道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以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完美的状态取代了人类的赎罪,以希望活在未来时代的记忆之中取代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不朽。”[3]然而,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早期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启蒙运动所追求的政治解放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把私有财产原则确认为基础的以自由、平等与博爱为普遍价值取向的理性国家与理性社会,因此,一方面,它在国家层面上造成政治国家的唯灵论,即国家的政治理念愈来愈抽象化和普遍化并日益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造成经济的唯灵论,即人们对金钱顶礼膜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野中,国家唯灵论与经济唯灵论构成了自由主义在实践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正是着眼于这两个方面的批判,而这又是以对宗教唯灵论的批判为前提的。马克思对这三种唯灵论批判的意图在于提醒人们要搞清楚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形态和观念形态之间的差别,不被抽象观念所支配而去做那种“希望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的“徒劳无益的事情”[4](p.204),从而唤醒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并废除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5](p.90),“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6](p.597)。
一、马克思对宗教唯灵论的批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言道:“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7](p.199)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s honne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7](pp.199-200)对马克思这段话的深层次理解,美国人悉尼·胡克是这样讲的:“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态度的本质当在那种实体的方法(method of hypostasis)中去寻找,不管被实体化的对象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引进这样一些抽象概念的做法都是宗教的,这些抽象概念的根源和所指被说成是先验的而不是历史的,……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科学方法,用以揭露那些因为引进了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而被掩盖了的人的问题和利益。他总是在问:那些非现世的和非经验的教条,其现世的和经验的基础是什么?在神学的抽象概念中,他看到了掩盖着特殊的历史需要和组织需要的一种语句拜物教。在法学的抽象概念中,他看到了掩盖着社会上真正的权力分配的一种原则拜物教。在经济学的抽象概念中,他看到了掩盖着人们今天受着他们自己所创造的那种生产力的支配这一事实的一种商品拜物教。每一套抽象概念都伴随着一套实践。这些抽象概念既然都是非经验的和非历史的,因此正只有依据这些实践才能指定它们的意义。”[8]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作为现实世界的精神支柱,它以抽象概念方式来把握现实世界,使得整个现实世界受着具有“灵性”的抽象观念的支配。具体地讲,不仅政治国家受着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政治信念的支配而具有唯灵论本性,而且作为政治国家基础的私有财产从精神的“他物”中抽象自己本身而成为“抽象的唯物主义”[7](p.111)之后也具有了“抽象的唯灵论”[7](p.111)特征,最终演变成为人们对它顶礼膜拜的“金钱拜物教”。
对于宗教唯灵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最初是从哲学认识论层面,即从“天象”与“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来阐释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借用伊壁鸠鲁的话指出:“人的心灵的最大迷乱起源于人们把天体看作是有福祉的和不可毁灭的,他们具有同这些天体相对立的愿望和行为。”[9](p.56)“因为行动与福祉不相一致,行动的发生大半与软弱、恐惧和需要有关”[9](p.57)。即是说,当人们认为天体有福祉且永恒不死,而人们以天体来反观自身并意识到自身不能像天体那样有福祉且永恒不死时,人的心灵意识到人自身在自然天体面前的软弱的同时就会产生恐惧感,心灵的迷乱使得人们崇拜神灵。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人把天和最高的地方划给神,因为唯有天是不死的”[9](p.56)。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神,不同民族的神是不同民族的人的自我意识的抽象产物。因此,一方面,对神的存在的证明就是对自我意识的证明;另一方面,谁本身无理性,神对他来说就存在。他讲道:“要是你把你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人们就会向你证明,你是受到幻想和抽象概念的支配。这是公正的。”[9](p.63)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明,都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谁觉得世界是无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无理性的,对他来说神就存在。换句话说,无理性就是神的存在”[9](pp.101-102)。
从阶级压迫的角度来分析宗教产生的原因,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经历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与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问题以及摩泽尔地区农民生活的困苦等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发生纠缠而导致“苦恼的疑问”产生时,开始从私有制与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世俗的苦难来分析宗教产生的社会政治原因,这在《德法年鉴》时期得到了集中的阐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7](p.200)在他看来,造成现实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财产制度及其与之相应的阶级统治,在这种关系中,“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7](p.208)。基于此,马克思强调:“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7](p.199)这里,马克思所言的“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指的就是人生活在“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国家共同体中。因此,“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7](p.199)。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人没有获得自身,没有得到享受,没有获得归宿感,因而只有在宗教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寻求慰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作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7](p.179)为此,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致卢格的信中特意强调:应“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10]
既然人们不能明白地把握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那么,马克思的结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7](p.199)这里,马克思所言的“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指那些“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7](p.179)。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讲道:“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11](p.97)
二、马克思对政治唯灵论的批判
在分析了宗教唯灵论产生的社会政治原因后,马克思讲道:“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7](p.200)在马克思那里,对启蒙运动在实践中所造成的法与政治的批判,可以说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来完成的。毕竟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是启蒙运动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法与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对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指出:“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7](p.22)“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政治上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具体地讲,黑格尔的做法是把政治制度(各种不同权力规定合乎理性的有机结合)看作是普遍观念(绝对精神)在国家领域的发展,即普遍观念向各种差别(各种不同权力以及各种差别的客观现实性,各种不同权力的职能和活动)的发展。结果是,黑格尔“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观念建立关系,把政治制度列为它的(观念的)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7](p.18-19)。
这种把政治制度理解为观念的发展史上环节的“露骨的神秘主义”必然使得黑格尔的官僚政治理论具有唯灵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特殊利益”同“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普遍东西(普遍利益)”之间的分离看作是一种矛盾,并力图通过官僚政治对这种分离及其所造成的矛盾进行整合,这是一种满足于从表面现象解决这种分离的做法,它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私有财产的问题,或者说,黑格尔的官僚政治维护的是抽象的私有财产。马克思问道:“政治构成、政治目的的内容……是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在长子继承权中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行使什么权力呢?行使这样的权力:政治国家使私有财产脱离家庭和社会,使它变成某种抽象的独立物。那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究竟是什么呢?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同这种本质相对照,政治国家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一种幻想:政治国家是规定者,可它又是被规定者。”[7](p.124)因而,“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最高的政治信念就是私有财产的信念”[7](p.123)。但是,在黑格尔那里,私有财产只是自由的绝对精神所外化为人的“抽象人格的权利”的客观化,而“抽象人格的权利、它的客观性、‘抽象的私有财产’,是作为国家的最高客观性,作为国家的最高的法而存在的”[7](p.134)。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出现了分离,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本质内容都是私有财产,政治国家以法的形式确立了“抽象人格的权利”的客观化的私有财产制度,使私有财产变成抽象的独立存在物,并且受“抽象人格的权利”抑或是抽象的私有财产观念的支配,从而成为维护抽象的私有财产的普遍的伦理国家。
因此,马克思指出:“‘官僚政治’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7](p.59)“既然官僚政治把‘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这样,官僚政治就是“国家的唯灵论”[7](p.60)。官僚政治实质是“各种实际的幻想的网状织物,或者说,它是‘国家的幻想’;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稣会精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官僚政治是僧侣共和国”[7](pp.59-60)。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7](p.111)政治国家要实现所谓的普遍利益,这是“抽象的唯灵论”;而市民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作为抽象的私有制,这是“抽象的唯物主义”。但是,作为“抽象的唯灵论”的政治国家要实现的普遍利益实质上就是作为“抽象的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成员所要求的特殊利益,因而,马克思讲抽象的唯灵论就是“抽象的唯物主义”;而作为“抽象的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成员的特殊利益往往被说成是作为“抽象的唯灵论”的政治国家所代表的普遍利益,因而,马克思认为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
由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7](p.173)因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7](p.42)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作为经院哲学,在于它把建立在私人物质利益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与人权观念变成市民社会成员的普遍的公民观念,也就是说,作为私人领域里的市民社会成员在作为政治生活领域里的法人或公民的时候被抽象的自由、平等与人权等观念所支配,但这种抽象的普遍的公民观念背后却隐藏着特殊的私人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诸如自由、平等、财产与安全等人权说成是利己主义的人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观念普遍化、抽象化的根源,即:“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5](p.99)但事实是,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道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p.274)而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抽象化宣扬而控制着社会成员的头脑并驱使着他们去追求这种抽象的、虚幻的自由。
三、马克思对经济唯灵论的批判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唯灵论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力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总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11](pp.89-90)很显然,通过劳动过程所创造出来的商品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11](p.88)的物,这是商品的一个重要的特质。说它是“可感觉”的,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显现,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同时它又是“超感觉”的,表现为“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11](p.88)。但正是由于商品的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特质,似乎意味着其本身就有着“生命力”并且天然地和人发生关系,据此,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并分析了“商品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具体地讲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2](p.426),也就是说,“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12](p.427)。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11](p.90)。而伴随着“商品拜物教”而来的则是“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
对于“货币拜物教”,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有所论及:“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7](p.194)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对金钱或货币顶礼膜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是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1](p.113)具体地讲就是,商品货币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越来越超越各种特殊商品的多样性而达到了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当它在充当价值尺度而对商品比较时只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当它行使流通手段职能时这种抽象又必须物化或象征化。“是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12](p.93)。同时,货币在行使储藏手段职能时,它是社会财富的直接代表,拥有了货币就拥有了一切。这样,货币的神奇魔力就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对货币占有者本身来讲,“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7](pp.361-362)。丑的男人可以用货币买到最美的女人,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人作为货币占有者因货币受人尊敬而使自己受人尊敬。一句话,“凡是我作为人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7](p.363)。总之,货币是“有形的神明”[7](p.362),它受人崇拜。但是,在货币神奇魔力的背后,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11](p.93)。
“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是在市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并且被我们深深感知的社会现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随着货币羽化为资本,拜物教的最高形式“资本拜物教”也成了历史使然。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11](p.171)即是说,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又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为了揭示“资本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商品流通的总公式“W-G-W”和资本流通的总公式“G-W-G’”的区别。前者是为买而卖,后者是为卖而买;前者是为了得到使用价值,最终目的是满足需要,后者的动机和决定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在后者中,货币实现了增殖,这个增殖被资产阶级称作是其合理的劳动所得。如果资本流通的总公式“G-W-G’”简化为“G-G’”时,资本就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的生息资本,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13](p.440),这是因为,“利息则好像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和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其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13](p.939)。由此,马克思讲道:“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11](p.227)
在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中,商品、货币与资本作为一种物的载体,呈现的是一种事实:人的自由与平等总是与资本所主宰的、与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密不可分的,因而,拜物教作为一种镜像,它折射的是物(商品、货币与资本)对人的自由与平等的生存方式的主宰,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实现直接依恋于物的事实。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当事人拥有商品、货币或资本才有可能拥有自由与平等,否则,则无事实上的自由与平等。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成员作为拜物教徒所推崇的自由与平等就带有虚幻的色彩,因此,拜物教彰显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唯灵论的本质规定。而经济唯灵论在资产阶级辩护论者那里,表现为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用纯粹抽象的思维来论证自由和平等。
四、马克思对唯灵论批判的意图
前以述及,马克思对宗教唯灵论、政治唯灵论以及经济唯灵论批判的意图在于提醒人们要搞清楚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形态与和观念形态之间存在的差别,不被抽象观念所支配,从而唤醒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意识。
就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矛盾而言,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等初期理论活动中是从法哲学与国家哲学这一“副本”的批判的层面来概括的,称之为“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开始从对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副本”的批判向政治经济学“原本”的批判进行过渡,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继续,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指认为“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个体与虚假的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并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来寻找这种对立的根源。而在《共产党宣言》与《雇佣劳动》中,马克思则自觉地从“原本”批判的角度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对立,这就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奠定了基础。在其中,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线,深刻洞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资本自身狭隘的生产形式使得雇佣工人“不是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12](p.541)。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就是它是资本(资产阶级的人格化)这一“死劳动”与雇佣劳动(无产阶级的人格化)这一“活劳动”之间的矛盾。“活劳动”使“死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的贫穷留给自己”[12](p.453)。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洞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才不会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产阶级观念所蒙蔽。反之,撇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就把握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形态,就不懂得历史辩证法,人们就会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抽象化了的观念所支配。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辩护者的全部的聪明才智不过是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用纯粹抽象的思维来论证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指责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受这种抽象观念的支配,天真地认为交换、交换价值在概念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企图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这种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4](p.204)。
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不断斗争的使命在于“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6](p.59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要求工人阶级要形成“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5](p.90)。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造成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之间的分裂的时代错乱,直截了当地指出它还不是更彻底意义上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必须过渡到人类解放。为此,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三大课题:(1)谁应当是解放者?(2)谁应当得到解放?(3)解放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对此,马克思的回答是:解放的承载者寄托于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把否定私有财产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唯有如此,人们才能从“虚幻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那么,真正共同体是什么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在思想上、在抽象中成为特殊利益,才有可能;而这又只有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7](p.61)这一主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它转换为如下呼吁:“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它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7](p.30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把上述主张用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这段话来表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18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10045);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BZZ008);河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GH753)。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
[3]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M].何兆武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12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02-10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4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苗贵山,河南科技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杨奕青,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