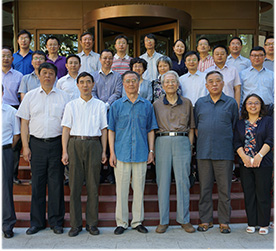[内容摘要]:马克思的宗教生产理论扬弃了亚当·斯密非生产性生产与黑格尔“精神生产”之说,既指向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生产,又兼有资本主义制度下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含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多生产要素,并且以包容认识论、实践论以及价值论的理论视野回应启蒙运动以降世界范围内宗教活动的各种新变化,对现代宗教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宗教生产;精神生产;历史唯物主义;宗教世俗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宗教学面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思想,并取得丰硕的实绩。然而,面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现代宗教发展更为世俗化的新常态,亟需重新审理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资源的理论基石。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宗教思想研究的历史、历史唯物论思想体系以及宗教生产思想的理论意义入手,论述马克思的“宗教生产”理论,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研究。
一、宗教生产理论与马克思的宗教思想研究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有关宗教思想的研究集中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中。马克思指出,以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德国纯粹宗教批判业已结束,而彻底的真正的宗教批判应当是法哲学和政治的批判。德国宗教批判致力于解决神圣世界与人的世界何以分离以及重新统合的可能性问题,其以“宗教的人”或以“神圣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分裂为前提,设想通过克服人的意识的异化来改变现实世界,而马克思则主张应从人的世界的现实性而非人的意识的异化出发来批判宗教,从而“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8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真正研究宗教的开始。
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彻底的宗教批判的开始,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向,而且表明马克思已从对德国纯粹宗教批判所秉持的对人之意识异化的批判转而探究现实异化的根源,进而提出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马克思在此虽未明言宗教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但是将它与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特殊生产方式并举实已暗示,宗教是一种非生产性生产或者精神生产,而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所支配。因此,设若认定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人的意识的异化的批判,那么此种意识的异化根源应当是现实生产实践中人的异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就思想史而言,马克思将宗教视为特殊生产的观点极有可能是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受到亚当·斯密影响的结果。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多次引用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内容。恩格斯称道亚当·斯密是“把一切——政治、党派、宗教——都归结为经济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5页)的经济学家,指出其著作中已然将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而“牧师”的活动即宗教活动就被视为一种非生产性劳动,即一种不生产任何使用价值的劳动。尽管宗教活动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劳动仍然受普遍的劳动价值原理支配。(参见王亚南,第384页)马克思对斯密的观点表示赞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43页)但他扬弃了斯密的相关论说,进而赋予“宗教生产”丰富的内涵。
一方面,马克思意义上的“宗教生产”指向一般社会分工意义上的精神生产,主要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一种幻想的、想象的精神生产方式。
追溯“精神生产”的概念史,此说较早出现在黑格尔《美学》之中。黑格尔谈及史诗时曾指出:“诗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黑格尔,第114页)而马克思则是在与恩格斯合作的《神圣家族批判》中最早提及“精神生产”之说,并初步阐述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所依据的相同原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2页)嗣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精神生产”的本质是“语言中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进而直接提出“宗教的幻想生产”之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5页)与此同时,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多次明确地阐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基本原理,而且已然视宗教为一种“精神生产”的方式,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并非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与物质生产的分离才成为可能。而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离也造就了最早的精神生产者——宗教神职人员,他们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同上,第35页)。因此,从精神生产的形式角度而言,“宗教生产”是人类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之一——宗教的掌握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2页),它主要是“在想象中和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同上,第761页),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不断生产意识形态或思想文化的重要力量。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精神生产与黑格尔所言的精神生产无论是概念内涵还是思维形式都有所不同。就“精神生产”的概念内涵而言,“精神”在黑格尔的思想谱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乎上帝、国家乃至思想、知识等诸多之物。精神兼有“实体”与“主体”之双重身份,其通过对世界或自然之创造否定自身,而克服自然之否定才能使精神具有新的飞越的可能。在此意义上,“精神生产”是最为基础的内容上已然完成的尝试,由此辩证地产生出世界的全部形式内容。而马克思通过将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扬弃为“劳动”,认为“精神生产”是社会大分工之后才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从动态而非静态、主动而非被动的维度揭示此种生产作为“当下本身中的真正的行为”发生在“过程”之中,而且此种总体的过程绝不会终结。就思维形式的维度而言,马克思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形式”是历史性的存在,马克思赓续斯密的作为经济学价值概念的“特殊生产”虽然存在于思维之中,但其本源则是“现实抽象”而非“思维抽象”,而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生产形式”则是思维的抽象,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使得精神优先于手工劳动,并且赋予其唯一的统治地位”(雷特尔,第8页)。由此可见,虽然“精神生产”的说法源自黑格尔,但是马克思赋予“精神生产”物质基础与历史性的内涵——此种“精神生产”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社会分工才能出现,因而此种“宗教生产”具有历史的、一般的含义。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专业化要求的宰制下,“宗教生产”具有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经济学意涵,主要是一种特殊的非生产性劳动,一般视宗教活动为一种职业化的生存或生活方式。马克思接着斯密之说进一步指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对于斯密所考察的东西——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精神生产中,表现为生产劳动的另一种劳动,但斯密并没有考察它。最后,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也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围之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5页)斯密只是关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生产性劳动,但是未予考察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非劳动性的生产,终至成为“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研究。马克思对此则进行深入的思考,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469页)资本主义的现实虽然“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98页),但是此种不合理的现实存在业已表明,历史维度的“宗教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方式已经拓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种职业的政治经济学的意涵。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活动便成为一部分人的谋生手段,成为一部分人所从事的职业。由此,马克思宗教生产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宗教思想研究合乎逻辑的内在发展结果。
二、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辩证关系中的宗教生产理论
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表述常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总说明。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原理来概述唯物史观。尽管两种唯物史观的含义是相同的,但其表述仍存在着细微差异,前一种表述是从哲学认识论的唯物反映观出发,后一种表述则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具有类似性。而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后一种表述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提到的“人的全面的社会生产”思想密不可分。
作为精神生产的宗教生产,一般总是受制于现实物质经济生产的制约。一方面从宗教生产的内在动机而言,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利益往往构成了宗教生产活动的物质动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强调:特定时代的宗教等思想是人们藉以意识到所处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冲突并力求克服它的意识形式。要真正理解宗教等意识形式的本质,我们就“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的冲突中求得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发生的诸多宗教事件每每受制于物质经济利益,以致恩格斯有所谓宗教为“神圣外衣”之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0-401页)总之,社会存在中物质利益之争委实成为人类历史上宗教活动的真正动因。另一方面,宗教生产的形式亦是与社会一般物质生产密切相关的。诸如在人类早期阶段,宗教是人对自然力的一种形象化把握方式,所谓“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53页)。而分疏人类早期宗教观念产生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主要是因物质生产的低下,造成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狭隘,于是“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中以经典性的表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1页)因之,宗教生产的形式作为社会关系的观念性表达本质上受社会物质生产所决定的,历史上宗教生产方式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的。马克思早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就指出:“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4页)而针对西方主要宗教基督教,马克思认为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嬗变的,并非社会发展随着它而变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39页),以致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一种具有封建教阶制的宗教。由此,宗教生产方式变迁的研究往往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方式。恩格斯晚年曾提出宗教发展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自然宗教-多神教-一神教”模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6-67页);第二种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提出的“自发的宗教-人为的宗教”模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第三种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部落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模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8页)。虽然三种模式的表述视角存在差异,但都是恩格斯有关宗教发展演变的重要研究,尤其是“部落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的概括更是对宗教生产模式的历史演变的高度总结。
宗教生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亦有相对的自律性。虽然宗教生产属于意识形态的生产,是“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但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宗教生产作为主要的精神生产方式对其他意识形态的生产发生重要的影响,甚至主导过该阶段的精神文化生产。以人类早期的自然宗教为例,马克思强调它对于希腊艺术生产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的重大命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0-761页)又如中世纪的欧洲,任何社会与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恩格斯曾指出:“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9页)。当然,恩格斯亦看到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作用:“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的巨大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同上,第321页)
宗教生产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具有一般性生产所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要素,即宗教生产组织、宗教生产方式、宗教生产主体以及宗教生产价值,各个要素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历史上作为宗教生产组织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经济组织。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古代人把神庙看作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2页注90)中世纪乃至宗教改革时期地产所有权维系着教会组织最核心、最基本的利益。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会曾拥有英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而罗马天主教会更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的三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7页)。因此马克思说:“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90页)除此之外,教会也享有如捐税和其他赋役等方面的重大特权和豁免权,而社会和教众的捐献也是教会组织的重要来源,以致教会如马克思言及犹太教在北美对基督教影响时所说的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7页)由此,教会作为巨大的经济生产组织不仅实践性地参与各种经济生产活动,而且形成规模巨大的“庙产”,以此巩固其宰制性的政治权力。
第二,宗教生产通过神职人员的精神性服务和教会组织的精神性产品满足信众的宗教需要。马克思曾指出新教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督教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生产方式,主要是因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和以商品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价值观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参见同上,第96页)宗教生产如一般的生产劳动也是“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4页)。它采用幻想的方式满足人的宗教需要,虽不具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也生产某种交换价值。它一方面是通过宗教神职人员直接给信众提供精神性服务,满足其正当需要,借以消除一般信众的心理恐惧和焦虑,使其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慰藉。另一方面,教会组织也通过宣扬宗教观念和教义精神的出版物、艺术品或者祛邪、免灾、赎罪券等具体的“精神产品”,来强化信仰、抚慰信众等。
第三,作为宗教生产活动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宗教情感是宗教信仰活动的关键。它不仅关涉主体自身的信仰活动,而且决定着以宗教的形式掌握世界的方式。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情感”,指出“‘宗教情感’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恩格斯则将宗教情感视为支配着自己的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而能够长久存在下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2页),从而恐惧感构成了宗教情感的核心内容。列宁亦指出:“‘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2页)因此,正是宗教情感的慰藉才构成真正的“宗教需要”,以致在新宗教创始阶段,“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9卷,第329页)
第四,宗教生产作为一般的精神生产具有认识价值、政治价值、艺术价值、伦理价值以及心理价值等多种价值形态。就其认识价值而言,马克思视其为人类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恩格斯则称其为自然和社会力量在人脑中“幻想的反映”,“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就其政治价值而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宗教“神圣外衣”论等,都是强调宗教以神圣的形式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功用的。就其艺术价值而言,马克思曾称赞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等。就其伦理价值而言,马克思指认基督教宣扬的“克己”“无比忠顺”“慈善事业”都是“建立在人类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之上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56页)。恩格斯则指出基督教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的复杂性,并将此归结为社会阶级地位的对立,进而提出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所体现的道德价值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3页)就其心理价值而言,马克思曾概括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等人的观点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参见赵敦华,第3-7页),此说主要指向宗教之于人的心理价值。尽管对于此说的含义历来的研究者聚讼不已,但是基本的认识在于“鸦片”喻指宗教正负两面的心理价值功能,一方面其成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工具,纾解其对现实的不满而生发的怨恨心理;另一方面宗教也给予苦难中的信众以心理乃至精神的抚慰,甚至终极关怀的功能。
三、马克思宗教生产理论的“包容性视角,为世界目的”
尽管哲学的认识论以及实践论视角,都曾对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细绎马克思主义宗教生产理论,它确实具有以精神生产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论特点。其既有对宗教现象的本质性透视,从而具有哲学认识论的视角,又有对资本主义宗教的政治经济学阐释,进而具有实践论特色,因此它包容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是一种宏观性的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价值论,亦是唯物史观贯彻于宗教问题研究的具体体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复如此,马克思的宗教生产理论就成为具有多重面向的体系性宗教理论。诸如从宗教的本质面向而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视宗教为一种幻想的反映,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一种精神生产的方式等;从宗教发展形态面向而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由“部落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的演变模式,认为宗教没有自己的本质,没有自己的独立史,宗教会走向消亡等等;从宗教的社会功能面向而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宗教是一种思想和精神慰籍等等。……设若单面地审视上述具体观点,难免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认为在宗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的(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390-391页),甚而指认马克思主义是非体系性的。(cf.Guglielmi,P.81)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宗教生产理论出发,那么上述思想片段就能够经得起体系性理论的阐释:其或者是针对宗教生产的动机,或者是针对宗教生产的内容和性质,或者是针对宗教生产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等,而且更符合现代宗教发展更为专业化的实践。
在现代宗教学研究中,对于马克思创始人的宗教研究亦常常会出现一些“印象式”的批评,诸如所谓“只有散见于各篇论著中的宗教观”,其宗教理论“实际上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附庸物”。如果不只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审视,那么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宗教生产理论不仅是一种“系统化为宗教学体系”的学说,而且因全面有力地回应西方近代世俗化进程中的最为基础的宗教问题,已然成为彼时宗教学研究的集大成。纵观西方近代社会的历史,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思想家深刻体认到近代世俗化之于西方宗教和庶民心理的重大影响,将宗教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来回应和阐释此一历史性事件。但是惜乎其未能把各种宗教问题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一端,从社会经济、政治等综合性研究中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进而理解“人的社会”的宗教的本质,正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的,“这最终导致两种视野——综合地、体系化地观察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相关之结构的视野,和对如何扬弃现实状况作出展望的视野——的丧失”。(柄谷行人,第1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宗教生产之论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辩证互动的理论基础上将社会学与宗教学研究相结合,以巨大的理论勇气通过对“人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面向的深度批判,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终至破解宗教的秘密,从而成为西方现代宗教学研究的典范。
当此人类社会步入晚期现代发展阶段之际,宗教更加世俗化的趋势已然促使宗教功能发生重大变化。宗教的世俗化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不再与政治、经济等领域利害攸关,宗教已退出公共领域,“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之域或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韦伯,第48页),而且还表现在宗教信仰虔诚度的下降,正如伊格尔顿所言,“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无信仰的”。(伊格尔顿,第11页)尽管部分群体由于对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焦虑与不满而导致希求“回到原初”的反现代性冲动,但是此种原教旨主义与世俗化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二者的逻辑并非相异而是相同。因此,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并非如彼得·伯格所言意味着“世界的非世俗化”,而是更加表征着世俗化进程的激进推进。某种意义上,这恰恰证明的是辩证法的成功而非失败。而此种世俗化的激进推进也促发宗教功能相较于此前时代发生重大变化。与早期人类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相比较,如今宗教的认识论功能十分有限;与中世纪宗教作为一种强烈政治色彩的权威意识形态相比较,而今宗教必须面对的是工具理性的促逼人之身与心的渐行渐远,以及现代性虚无主义所孽生的价值相对主义的风险,如何重建道德理想国覆灭之后新的伦理道德,怎样突破“人为物役”的现代性困境,乃是一个日益突出的世纪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5页)其实,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非止于现实性上人的个性化的主体消解、还原于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之中,更重要的是人之人文理想性——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现时代的宗教已然面临调适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使命,即要成为参与建构马克思意义上人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更为明显的是,为当代文化工业所裹挟的宗教也竟然成为最流行的文化之一,以致形成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的宗教文化产业。某种意义上,随着20世纪以降文化工业的急剧发展,宗教最终以电影院、电视机、广告和大众出版的形式实现了。面对此种现状,单向度地从认识论、宗教学的维度来诠释宗教问题已然远为不足。而马克思的宗教生产理论作为一种奠基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具有价值论色彩的宗教理论体系,不仅以包容性的视角、体系性的言说走出了哲学认识论、宗教学等理论维度阐释的困境,而且积极回应世界范围内宗教发展的实践,从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结语
伊格尔顿曾援引马克思之语强调“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马克思将宗教视作人民的精神鸦片,同时还是牧师洒向资产阶级腐败良心的圣水。而不那么广为人知的则是,他还将宗教视之为这个失去心脏的世界之心脏。”(伊格尔顿,第92页)然而马克思并未从一般意义上的无神论出发否思“上帝之在”,因为马克思深谙“上帝的缺位或许通过对人的迷信而弥补了,但是那个被丢弃的上帝最初看上去也不过就是一个迷信”(Miller,P.143),他通过更深层次地探寻这个“世界心脏”的“现实来源”——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劳动实践等,不断深掘自我塑造的主体之物质本源,以此建构其宗教生产理论,进而批判性地深度揭发现实存在中的“人的异化”。在此意义上,有别于孔德等宗教学家以及标举“超人”类宗教之神的尼采,马克思所揭橥的宗教生产理论作为一种奠基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具有价值论色彩的宗教理论体系,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今宗教发展进程中所表现的种种新变,重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深具阐释力的宗教生产理论,这既非某些群体的激情呐喊,发愿以重新解释马克思来包治现代宗教之痛,也非另一些群体所检讨的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从马克思本身出发,释放出马克思主义原生态理论的思想魅力与阐释力度,为中国和世界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柄谷行人,2012年:《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2.伯格,2005年:《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李骏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3.费尔巴哈,2010年:《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4.黑格尔,1981年:《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5.雷特尔,2015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6.《列宁全集》,1988年,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57年、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1965年、1971年、1972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9.王亚南主编,1979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
10.韦伯,2005年:《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
11.伊格尔顿,2016年:《文化与上帝之死》,宋政超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12.赵敦华,2014年:《宗教批判也是马克思批判思想的前提吗?——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特点》,载《哲学研究》第1O期。
13.Guglielmi,1964,Avanguardia e sperimentalismo,Milan:Feltrinelli.
14.Jameson,F.,2012,A Singular Modernity,London.
15.Miller,J.H.,1963,The Disappearance of God,Cambridge.
*本文系西安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重大培育课题“颓废与审美现代性研究”(编号SKZD16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妥建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杨庙平,广东韩山师范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