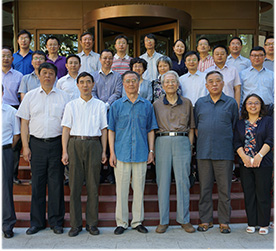[内容提要]:金代寺院的财产来源以继承前代和信众施舍为多,房舍、土地、树木园林是寺院的主要资产,部分寺院还依靠借贷取利。寺院田产经营主要采取自耕、佣耕以及由“二税户”耕种等方式。遇有土地纠纷,有的由纠纷双方自行调解,有的通过诉讼渠道诉诸官府。田产石刻往往成为解决财产纠纷的重要证据。寺院需要缴纳赋税,一些有权势的寺院竭力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规避赋税。
[关键词]:金代;佛教寺院;经济生活
自魏晋以来,寺院经济渐成规模,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学术界对金代寺院经济的研究还非常有限[1],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金代寺院经济进行系统探索。实际上,寺院经济是金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寺院经济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金代经济的全貌,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金代佛教生活。因此,笔者不揣愚陋,拟以金代寺院经济的若干见解求教于同好,恳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寺院财产的来源
中国古代的佛寺大都拥有或多或少的财产,究其来源,以信众施舍、寺院租佃与购置为多[2]。金代寺院财产的来源与此前各代大致相似,从总体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渠道:
(一)继承前代财产
金朝初年的佛教寺院大都继承自辽和北宋,而辽、宋又是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很多寺院都拥有巨额资产,以辽为例,蓟州感化寺“以其创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粟万余株”,该寺在三河县北乡的一处寺庄“辟地三十顷,间艺麦千亩,皆原隰沃壤,可谓上腴”[3]。在辽代的寺院庄田中,感化寺的规模并不算大,一些名寺巨刹接受皇帝或上层贵族捐赠的土地动辄数百亩甚至数千亩,大安五年(1089)道宗敕旨,赐觉山寺“山田五处,计一百四十余顷,为岁时寺众香火赡养之资”[4]。咸雍年间,义州大横帐兰陵郡夫人萧氏捐资创建静安寺,工毕后,“遂施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5],这些在辽代积累起来的寺产入金后成为金代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例如义井寺的田产中就包括了辽代崇宁年间大檀越故赠武义大夫韦公所施田地三百亩[6]。大天宫寺于辽代清宁年间获赠“墅地二千四百亩,南墅地二千五百亩,用给斋厨之需”。这些土地入金后依然属于大天宫寺的财产,“二墅之地,籍隶佛土,凡传授本未,有敕牒券记在焉”[7]。金代一些历史悠久的寺院其田产起源更早,例如宝山寺,自北魏以来就屡获朝廷颁赐,“大魏武定四年,敕赐宝山寺常住白药石山等地土”,“大齐天保元年,敕赐本寺白药石山一座”,“大隋开皇五年,敕赐宝山灵泉寺白药石山等地土”[8]。古贤寺的庙产一部分来自唐代朝廷赏赐,“贞观三年赐熟田五十顷以为常住”[9],这些庙产虽然历经朝代更迭,但由于寺院犹存,地土传承有序,因此,直至金代仍然是寺院田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信众施舍
按照佛教观点,向寺院布施以供养三宝是获得来生福报的重要方式,受此影响,金代佛教信众不断向寺院施舍,从而为寺院赢得大量财产。这些施舍多种多样,有的仅仅是一条石柱,如泰和元年(1201)九月,西张次村董志博家合宅施予华严寺石柱一条[10]。有的是一块坟地,如《浦公禅师塔记》的碑末题名中就有施坟地弟子曹本仁等人的名字[11]。有的是施一方蔬圃,如金末元初,遭兵火之灾的燕京大觉禅寺在奥公和尚住持下得以复兴,八方信士纷纷施舍,“有提控晋元者,施蔬圃一区,于寺之南,以给众用,糊口粗给”[12]。有的则施给田地,龙岩寺重修大殿时,“以遗址狭隘,艰于修完。下有桑田,昔为吾家祖业,至天会九年辛亥先祖父赵卿暨叔礼施为金田”[13]。金朝初年,泽州信士有感于松岭禅院僧人宗愍舍身护法,遂慷慨施捐,信士刘严“乃舍安庄社山庄一所,敬施山门,以充常住”,居民张权“施梨川社田五顷,俾供佛僧,以资冥福”[14]。大定年间,鄄县营建正觉院时,“其寺地田少缺,复有善知识杜与归其邻田”[15]。上述普通信众虽然有强烈的向佛之心,但毕竟经济能力有限,因此捐施数量有限。与他们相比,一些皇族及王公巨卿给寺院的布施往往相当可观,例如大定二十四年(1184)昊天寺建成时,大长公主“给田百顷”[16]。
金代一些没有子嗣的信众有时还将身后田产赠与寺院。大阳资圣寺获得的一份地产就来自一位无子嗣者,“本社宋阿李生前为无后,将本户下地土一顷五十余亩施与本寺充常住”[17]。信众施舍田产是出于佛教信仰,从形式上说,这些捐赠应该是无条件的,但从石刻史料的记载来看,无子嗣者的捐赠却有明确的目的,例如,要求寺院在捐赠者本人去世后,为其追荐冥福,代祭先祖。据刻于承安二年(1197)的《施地碑记》记载,“沁州武乡县岩良村住人刘方,今为年老,别无房亲子嗣,恐方百年之后无人追荐福囗,将自己户下住宅后中光至何家白地七段约八顷余,施与禅隐山崇胜寺住持僧从寿,永为常住耕种”。这次布施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求从寿等人在刘方去世后代他祭奠历代先祖及亲属家眷,为约束双方,“今将所有地土亩垄、祖先以下姓名开立在前,恐后无凭,故立施状为据”[18],佛教信众给寺院的施舍本应是无条件的,刘方以代祭先祖为前提的布施既是布施的一个特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寺院社会公益功能的延伸和扩展。无论这种捐赠是否设定了前提,它的结果是相同的,即信众的捐赠最终化为寺院财产。
寺院是传播佛教的主要场所。金代中原地区的佛教虽屡经战火摧残,但旋灭旋兴,究其原因,社会大众捐资献力,积极参与寺院的创建和修复是一个重要原因。善男信女们为修建寺院竭尽所能,往往一人振臂,群起响应。从石刻史料的情况来看,金代社会大众协助创修寺院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直接将宅第施舍给僧人,如世宗时期,“秉德既死,其中都宅第,左副元帅杲居之。杲死,海陵迁都,迎其嫡母徒单氏居之。徒单遇害,世宗恶其不祥,施为佛寺”[19],又如金朝末年“抟霄元帅筑西庵于厅事之隅以舍沙门”[20]。有的捐献金钱,如重建凤山梵云院时,于弁、刘收等七人“各施钱百千,为塑绘之费”[21]。有的捐献地基,如修武县张陆村修缮寺院时,邑人李善“性乐空门,见仪像颓败,寺基尽为陇亩,特发诚心,买到税业地三亩,率其同志,复展新基,再修禅宇数楹”[22]。有的协助募集善款,如重修太行古贤寺弥勒殿时,邑众三十余人“又除自己净财外,各人分头诱化,自近及远,多方求访”[23]。有的捐钱为寺院购买名额,如大定三年(1163)沁州铜鞮县王可村大户“孙庚等办施钱十万,赎得‘昭庆院’额”[24]。更多的普通百姓则献工献力,即所谓“壮者施力,匠者施巧”[25]。由于佛教信众的捐资助力,一座座伽蓝才得以拔地而起,离开他们的支持,金代佛教就不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
(三)朝廷赏赐
朝廷赏赐是寺院财产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一些皇家寺院或者具有重要影响的寺院所受赏赐更多。从现有史料来看,朝廷赏赐寺院以世宗时期的次数最多。大定二年(1162),大庆寿寺落成时,世宗“赐钱二万,沃田二十顷”[26]。大定三年(1163),世宗命晦堂大师俊公主持中都大延圣寺,“内府出重币以赐焉”[27]。大定十年(1170),“金国世宗真仪皇后出家为尼建垂庆寺,度尼百人,赐田二百顷”[28]。大定十三年(1173),“东京垂庆寺起神御殿,寺地偏狭,诏买傍近民地,优与其直,不愿鬻者以官地易之”[29]。大定二十年(1180)正月,“敕建仰山栖隐禅寺,命玄冥顗公开山赐田”[30]。大定二十六年(1186)三月,香山寺成,世宗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粟七千株,钱二万贯”[31]。从这几则史料来看,世宗赏赐寺院几乎贯穿大定始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世宗对佛教的态度。除世宗以外,金朝其他皇帝当政时也有赏赐寺院的零星记载,天会年间大延圣寺初建时,“帝后金钱数万,为营缮费”[32]。章宗游览仰山栖隐禅寺后,“遣使赐钱二百万”[33]。崇庆元年(1212),奉卫绍王圣旨,赐中都竹林禅寺“钱钞二万贯,麦四百石,粟三百石,石盐一百袋”[34]。
金代寺院财产的来源多种多样,除以上几个主要渠道以外,一些寺院还会向官府或民间购买土地,金朝初年圆教院主僧就“请囗到招贤坊空闲官地弌段,计陆拾陆亩,环筑垣墙作院子居止”[35]。大定年间,“坊州中部县王家庄王山、王万,今将堡坡头全分庄寨地等施不留,土木相连,尽行出卖,计铜钱九百七十三贯省。(中略)四至并全出卖与石寺院李善晏,充寺常住”[36]。有的寺院还倚仗自己的势力巧取豪夺并放债寻租,课取厚利,《平原县淳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就记载:“昔有为僧者,往往指射佛宇,诳诱世财而乾没者有之,市膏腴之田为子孙之计者有之,举息与人而获厚利者有之”[37]。此外,金代一些寺院的田产也来源于垦植荒地。由于禅宗农禅合一的传统影响,加之一些寺院修建于地僻人稀之处,有许多荒闲土地可供耕垦,因此,开荒垦植也是金代寺院田产的又一重要来源。比较来看,在本文述及的几种寺院田产的来源渠道之中,以前代继承和信众施舍最为常见,也最为重要,朝廷赏赐更多地集中于那些名寺大刹,而中小寺院一般无缘获赐,至于寺院自购、开荒垦植则要受到寺院自身经济实力的制约。
二、寺院财产的种类与规模
佛教虽是出尘之学,但毕竟要生长在俗尘之中,离不开万物的滋养,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因此,佛祖允许弟子在一定条件下从事商品买卖等活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若诸弟子无人供须,时事饥馑饮食难得,为欲护持建立正法,我听弟子受蓄奴婢、金银、车乘、田宅、谷米,卖易所须”[38]。佛祖允许弟子从事商业活动的本意应是为了安身立命之用,但魏晋以后,寺院财产渐多,大至名寺广刹,小至山野草庵,佛教寺院都拥有或多或少的财产,由此构成了寺院经济。寺院经济的种类及规模则因寺院的不同而不同。
就金代情况来看,房舍是僧人赖以栖身之所,也是寺院最重要的不动产。僧寺房舍的多少则因寺院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怀州明月山大明禅院有“大小屋舍一百余间”[39],金末长清灵岩寺“有屋三百余间”[40],平遥慈相寺经过重修后,拥有屋宇“凡一千二百余间”[41]。而一些小规模的庵院,如泽州普照禅院仅有“佛堂计壹拾贰间”[42]。
土地是寺院的又一项重要资产,不同寺院的土地数量对比悬殊,漫真村宁国院“寺业相承,膏腴三十八亩”[43]潞城县云岩山崇庆院“赐紫悟明大师营雄田一百双以给堂下”[44]王山十方圆明禅院有“甓门膏腴几三百亩”[45],泽州硖石山福严禅院“有山田二千亩”[46]。上述寺院拥有的土地,少者数十亩,多者数千亩,相差不啻天壤,这也是佛教僧团贫富分化的缩影。
金代一些寺院拥有大片树木园林,这也是寺院的重要财产。凤翔府青秋乡槐芽社惠济院有“古槐树四棵,柏树四十八棵,索罗树一棵,药树一棵,苦莲树一棵,柿树三棵,其小树不计”[47],该则史料没有介绍惠济院的地产数量,而是详录各种树木情况,这说明惠济院的寺产以林木为主。除了种植槐、柏等用材林,有些寺院还大面积种植经济林。中都大庆寿寺种有粟园,“祖师以华严经为字号种之。当身迷望,岁收数十斛,为常住供”[48]。有些寺院果蔬兼种,如漫真村宁国院在地亩之外,“于寺宇植杂果树百余本,蔬圃百畦,四方游学而至者咸有所济度”[49],这样既能自给自足,又能利养游学。
放债取利向为世人所恶,更应为佛徒之忌,但佛法对赚取钱财并非一味排斥,而是有条件地允许,《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22云:“世尊告曰,若为僧伽,应求利润。闻佛语已,诸有信心婆罗门居士等,为佛法僧故施无尽物。此三宝物亦应回转求利,所得利物还于三宝而作供养”[50]。佛法对僧人取利虽然是有条件的,但先例一开,难免泥沙俱下,经商遂成为寺院及僧人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寺院还将巨额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放贷取利,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谈到宋代寺院的高利贷经营时说“今僧寺辄作质库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51]。金代史料中关于寺院经营借贷的个例虽然极少,但仍能反映金代寺院借贷的概貌。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提到:“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52],一座寺院就拥有28所质坊,可见当时寺院借贷规模之大。同书又云,“有银珠哥大王者,以战多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53]。数十之民欠一僧之债,足见该僧的富有,而放债竟至六七万缗,也足见僧人放债规模之大。金代寺院不仅以金钱放债,亦以贷粮取利。《金史·卢孝俭传》云,卢孝俭为广宁尹时,“广宁大饥,民多流亡失业,乃借僧粟,留其一岁之用,使平其价市与贫民,既以救民,僧亦获利”[54]。
佛教寺院作为僧人的栖止之所,除以土地出产粮谷,以山林出产果蔬,还通过设立碾坊、油坊等来获得其他生活必需品,由此形成了寺院手工业。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对金代寺院手工业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幸而近年来的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201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云冈石窟窟顶一处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中,发现了辽金时代的铸造工场,这是迄今国内辽金时期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铸造工场。据专家介绍,这座铸造工场与辽金寺院建设有密切关系[55]。宋代史料中有寺院经营冶金、金属加工业的记载[56],由此推断,云冈石窟发现的辽金寺院铸造遗址也可能与寺院手工业有关。
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金代寺院经济虽有一定规模,但与两宋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与金代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尽管如此,寺院经济仍为金代佛教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三、寺院田产的经营方式
田产是佛教寺院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这些田产需要妥善经营才能满足僧众日常所需。当田产遭到破坏或侵夺时,也需要以适当方式维护寺院利益。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金代田产的经营与保护做系统研究,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有限史料的发掘与分析,描绘出金代寺院田产经营的概貌。
按照寺院拥有土地数量的不同,金代寺院田产的经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自耕
禅宗有农禅结合的传统,劳动耕作既是僧人参禅修行之道,又是僧人生存自养之途。自道信、弘忍以来,随着禅宗农禅理论的不断完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逐渐成为禅门家风,即使一些高僧大德也经常亲执劳役,勤苦耕耘。金代一些寺院的僧人在寺业初创时期尤其如此,例如泰山附近之谷山寺,屡经兵荒,“残扰殆遍”,当该寺初祖善宁来到此地时,见到的不过是“破屋废圮而已”。但善宁不为艰难所阻,决意亲执劳作,重兴寺宇,“于是日趋山下,匄菽粟,携火具,结茅而休焉。往来山坂无难色,暇日畚筑溪涧,勤苦作劳而无怠意。短褐芒履,从事如初”。善宁辛勤垦作三十余年,换来了丰硕成果,“自是涧隈山胁,稍可种艺,植粟数千株。迨于今充岁用焉。斋粥所须,日益办具”。继善宁之后,二祖法朗不缀农禅本色,“锄理荒险,不避寒暑,经营成就,复卅余年”,其后崇公“经画作劳,能继二祖”[57]。谷山寺三代僧人皆能躬行作务,它所体现的不仅是禅宗本色,更反映了寺院初创时期僧人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及辛勤耕作经营寺院田产的精神风貌。与寺院初创时的筚路蓝缕相似,金末诸事凋敝,很多佛寺受战火影响,生活难以为继,一些僧人不得不亲自从事生产,龙兴汴公禅师于“龙兴焚荡之余,破屋数椽,日与残僧三四辈灌园自给”[58]的生活经历就是金末僧人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亲执农桑的真实写照。
以上史料反映的是特殊时期僧人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由于史料的限制,尚无法判断自耕经营在金代寺院田产中的比重究竟如何,但可以推断,在那些只有少量土地的寺院中,僧人自耕应是寺院田产经营的重要方式。
(二)佣耕
如同世俗社会中田地较多的农户需要雇人耕种一样,金代的一些寺院也实行佣耕。平遥县慈相寺“东南原有别业数百亩,恒苦远治,乃构屋数十间,就召耕佣,遂为便易”[59],看来慈相寺募人耕佃的原因是田地距寺颇远,耕种不便。与佣耕相似的还有“住佃”,即把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户经营,宁夏固原县须弥山石窟所记大定年间重修景云寺题记写有“……售有人住佃随人地据”字样[60],可为金代寺院田产实行住佃制的样本。
(三)由“二税户”耕种
金代的“二税户”系由辽代演化而来,关于辽代二税户,史料有两种记载。其一,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曰:
初,辽入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61]。
从该段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此处的“二税户”是指辽代头下军州二税户,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二税户”,有学者认为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实行两税法,称缴纳两税的农户为“二税户”[62],而辽代加以沿用之故。但从上引《中州集·李承旨晏》的情况来看,所谓“二税户”未尝不是一方面输租于官,另一方面又纳课于主,两税皆纳之意。至于辽代“二税户”的确切涵义,可以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金代与寺院有关的“二税户”并非《中州集·李承旨宴》所记“二税户”,而是另有所指。《金史·食货志》云:
初,辽人侫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63]。
该段史料提到的“二税户”与辽代头下军州二税户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是借用了辽代头下军州二税户的称谓而特指寺院二税户。辽代以良民赐诸佛寺的事例并不少见,如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行状碑》就记载道宗时期秦越大长公主耶律氏曾向拟建中的大昊天寺捐施“户口百家”[64],刻于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也提到兰陵郡夫人萧氏曾向静安寺捐施“人五十户”[65],按照《金史·食货志》的说法,这些民户在被捐施给佛寺后,其收成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成为寺院二税户。辽金鼎革之后,由辽代沿袭而来的寺院二税户制度并未废除,而是继续沿用,二税户由此成为金代寺院田产的重要耕耘者。这一制度到世宗初年开始动摇。世宗继位不久,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大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从大定二年(1162)开始,“诏免二税户为民”[66]。但这项改革的进展并不顺利,“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67],寺院作为二税户制度的受益者,当然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杀伤人命。同时,由于寺院二税户制度由来已久,一些政府官员对二税户的申诉也置若罔闻,以致“诉者积年,台寺不为理”[68],时任御史中丞的李晏得知这一情况后,上书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良’,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69],寺院二税户制度由此趋向没落。章宗即位初年,“议罢僧道奴婢”,朝野再次就寺院二税户问题展开讨论。以太尉徒单克宁为首的一方主张循序渐进,逐步废除僧道奴婢,其理由在于“此盖成俗日久,若遽更之,于人情不安。陛下如恶其数多,宜严立格法,以防滥度,则自少矣”。另一重臣完颜襄主张立刻废止僧道奴婢,其理由是“出家之人安用仆隶?乞不问从初如何所得,悉放为良”。章宗最终采纳了完颜襄的建议,“由是二税户多为良者”[70],寺院二税户的问题才就此解决。
四、寺院田产的保护
土地是阖寺僧侣的衣食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同世俗社会一样,随着世代迁移,时光流转,寺主易人,寺院土地也面临着被侵占、典卖等诸多风险,明昌年间,奉先县六聘山天开寺就发生过寺院“四至内林木被诸人强行斫截”的情况,虽经寺院僧人诉至官府,但诸“贼人”仍然“强行斫截及搬运柴木,蹬损梯道,每日相持,无有定度”,甚至“每发恶言,要斫坏梯道,断绝路径”,在“贼人”的威胁下,天开寺僧人“常是怯惧,不敢早晚出入”,以致寺院因此而“山门日渐凋敝”[71]。受到“贼人”威胁的不仅是天开寺,即使长清灵岩寺这样名寺巨刹的财产也不免遭受侵害,“寺有赐田,经界广袤,岁月迁讹,颇见侵于其邻”[72]。民间不法之徒侵夺寺田,虽时有发生,但造成的后果总是有限的,而国家在一些特殊时期侵占寺院田产带来的损害则是毁灭性的,例如,正隆元年(1156)二月,因猛安谋克土地不敷分配,海陵派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巡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等地拘括各种土地,其中就包括“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73]。章宗初年,为搜集铸钱所用铜料,派人勘探铜矿,“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74]。上述来自民众、政府的种种不法侵夺,尤其是政府侵夺,构成了对寺院田产的巨大威胁,寺院为了保证田产能够世代相传,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
金代寺院遇有土地纠纷,有的由纠纷双方自行调解,长清灵岩寺田产被侵时,管勾灵岩寺寺门事传法妙空大师“不与之争,而谕之以理”,侵占寺田者为妙空的修养和度量所折服,“皆尽归所囗田”[75]。但类似妙空这样的例子仅是少数,当争议双方无法达成和解时,只能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例如六聘山天开寺山林被人强行采伐时,主僧善惠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于官告给引文榜付本寺收执,为主照使”,“先告引万宁县文收执为验”[76]。当寺院在田产诉讼中取得胜利后,往往要勒石刻碑以纪其事。所谓勒石刻碑是指寺院将寺田四至及地上附着物的情况镌刻在石碑上,以立石为信的方式保留和固定寺田属寺院合法财产的有力证据。但寺院为寺田立碑不可随意而为,而是有条件的,即:寺田必须首先获得官给凭贴才可刊碑立石,多方金代石刻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罗汉院山栏地土公据》载,金末罗汉院监寺僧广源状告前长老普润将带本院常住地土公贴凭验等逃往他寺,严重威胁了罗汉院田产的安全,为防止“他人已后侵占本院山栏地土以致昏赖,旋难争理”,广源遂将此事提告到县,经有司审理,认为“僧广源所告委是端的,亦无诈冒”,于是“出给公据,付净惠罗汉院监寺僧广源收执”[77],获得官府公据后,典座福信、监寺福蒙、首座定宣等刻碑立石,将上述原委及寺田八至俱刻石碑。《重修法云寺碑》也记载,法云寺住持福灯“自天德二年,贞元元年,两次经本军陈囗囗乞存留余囗公据二本”,公据内载明山栏地土四至,“至大定八年,又经本县告状出给公据”[78],法云寺遂刊刻石碑,详载其事。
金代佛教信众时因各种原因将个人土地施捐寺院,为避免日后争执,有效维护寺院田产的安全以及捐赠人的意愿,有时亦将施捐土地的四至、面积、地上物产等刊刻立石,比较典型的如《施地碑记》详记了沁州武乡县岩良村刘方施予禅隐山崇胜寺住持从寿土地的情况。从碑刻的情况来看,这些土地共“七段约八顷余”,碑刻详列了每段土地的四至,竭力做到“各段四至,各各分明”[79]。
金代一些大型寺院通过不同渠道占有大量房屋、土地,将这些房屋土地的情况立碑刊刻,实际上是保留了寺院的田产明细,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寺内不肖之徒隐瞒、典卖土地,《大宋河中府中条山万固寺重修碑铭并序》碑未有云:“以有古迹名碑为照,以后法属徒众遵崇看守依禀者”[80],实际就是要求后代子孙谨守寺产,永续田土。另一方面,当寺院与世俗社会发生田产纠纷时,碑刻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从而维护寺院利益,《灵岩寺田园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灵岩寺为自古名刹,经历代赏赐,寺产众多,土地的出产成为灵岩寺僧众衣食之源,“虽四方布施者源源而来,然其衣食之用,出于寺之田园者盖三之二”,田产对灵岩寺的重要性不问可知。但是,灵岩寺的大量田产也引起了他人的垂涎。北宋天圣初年,灵岩寺田产被侵冒,“主寺者,不克申理,但刻石以纪其当时所得顷亩界畔而已”。主寺者的态度显然过于消极,这种仅勒石刻碑而不向官府提告的行为不可能维护寺院的正当权益,只能导致侵冒行为愈演愈烈,后来绍圣时期灵岩寺的田产就遭到进一步侵夺。但是,天圣石刻毕竟是当时寺院田产的真实记录,它为以后解决这一纠纷提供了重要证据。果然,到伪齐时期,“始征天圣石记,悉归所侵地”,天圣石刻终于在维护灵岩寺田产的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由于天圣石刻字迹斑驳,寺僧因请于有司,主首与故老近邻再次立石刻碑,是为“阜昌碑石”。海陵天德年间,“复有指寺之山栏为东岳火路地者”,在这起侵占案中,阜昌石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既而,省部委官验视,考之阜昌碑文,不得遂其诈”。“大定六年(1166),朝廷推恩,弛天下山泽以赐贫民”,一些寺院山林由此遭到严重破坏,“惟灵岩山林,以其有得地之本末,故独保完”。明昌三年(1192),“提刑司援他山例,许民采伐”,灵岩寺山林再次受到严重威胁,“由是长老广琛诉于部于省,才得地之十一二也”,明昌五年(1194),广琛“复走京师,诣登闻院陈词”,在这起诉讼中,石刻再次为维护寺院田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蒙奏断用阜昌天德所给文字为准,尽付旧地”,这次诉讼结束后,灵岩寺深感碑刻对维护寺产的重要性,遂将官府所给公帖“复刻石,以为后人之信”[81]。自北宋至金代中叶,灵岩寺田产屡次被侵,在维护寺田的几次诉讼中,田产石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寺院赋役
寺院田产虽是僧有之物,但同时也是国家税赋之源。自佛法传入中土以来,国家不仅致力于在政治上强化对佛教势力的控制,而且在经济上也不断加强对寺院的管理。以赋税差役为例,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一些官僚贵族为扩大佛教影响不惜以免除赋役招徕信徒,三国时期的笮融就曾“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82],但是,僧侣“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83]的特权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利益,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政府的打压,唐代实行两税法之后,“天下庄产,未有不征”[84],僧尼经济特权由此走向衰落。寺院僧尼先是失去了免纳杂税的权利,两税法之后又丧失了免纳正税的权利[85]。及至南宋,僧尼“免丁钱”的征收更是寺院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僧道原来享有的种种经济特权被彻底剥夺干净[86]。
金代寺院缴纳赋税整体情况虽然未见详细记载,但据零星史料推断,金代寺院也需要缴纳赋税,大定年间,宝山寺主僧“于地内拔地参亩与师侄惠安充修院地”,《宝山寺地界记》明确记载了该段土地的分布及四至,并言明:“又承管王琪白石地四十亩,八亩熟土,纳秋粟二斗,物力钱十文。宝海立文字与宝山,每年出税钱二贯”[87]。史料中提到的“秋粟”是金代正税之一,宝山寺的土地须纳“秋粟”说明金代寺院土地需要缴纳正税。物力钱方面,金代规定“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88],这实际上是政府根据各户的田产、浮财数量经折算后征收的资产税。《金史·食货志》将物力钱的征收对象仅限于“民”,而未言及“僧”,但从《宝山寺地界记》所云,宝山寺须纳“物力钱十文”的情况看,寺院田产也需缴纳物力钱,此外,章宗初年议论寺院奴婢应否废除时,完颜襄建议“若寺观物力元系奴婢之数推定者,并合除免”[89]。这些史料说明,至少在章宗以前,寺产既要缴纳赋税,也要缴纳物力钱,而且寺院奴婢数量与物力钱多寡有关。
寺院既然同世俗社会一样承担国家赋税,则其设法逃避赋税也不可避免,同时,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对寺院免征赋税的事情也偶有发生。皇统年间,定光禅师住持长清灵岩寺,到寺不久即赴官府请求减免科差,曰:“常住拔赐田土,亲力播植,所得仅足饱耕夫。又供僧岁费,无虑三千万。丐依旧例,原免科役,庶获饭僧福田,上报国恩,实远久之大利益也”,定光以灵岩寺僧众开支浩大为由,请求官府依例免除科役,“府可其请”[90]。定光采用合法手段请求免除灵岩寺科役,这同唐宋以来的情形一样,一些有权有势的寺院竭力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来规避赋税,而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小寺院无法享受到这些特权,只能在沉重赋役的剥削下苟延岁月。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金代寺院经济有一定发展,但与此前的唐、北宋、辽相比,金代寺院经济的规模有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受制于金代社会经济的整体水平。应当说,直至金末,金代一些地区的经济还未恢复到北宋时期的水平,加之连年战乱,导致社会能够提供给寺院的经济资源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和金代佛教自身发展程度相关。高宗南渡后,中国佛教重心转移到南方,北方佛教未能有大作为,社会影响有限,能够吸引到的经济资源也自然有限。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加以考虑:金代道教的繁荣对佛教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进而也分流了一部分潜在的寺院经济资源。尽管如此,金代寺院经济作为中国寺院经济史的重要一环,也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心力,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代佛教研究”(12BZJ006)
注释:
[1]学术界对金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朝廷对寺院的赏赐、信众对寺院的施舍等方面,如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第5辑,1996年);王新英:《从石刻史料看金代佛教信仰》(《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王德朋、王萍:《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北方文物》2015年第2期);刘晓飞:《吾以尘缘事梵刹——试析金代汉族家庭的宗教信仰》(《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等。上述成果并非探讨金代寺院经济的专文,只是作者研究金代佛教时,在行文中对金代寺院经济有所提及。
[2]宋辽金时期寺院的财产来源,参见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白文固:《辽代的寺院经济初探》,《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崔红芬:《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上方感化寺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3、564页。
[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重修觉山寺碑记》,第689-670页。
[5][6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创建静安寺碑铭》,第362页。
[6]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义井寺崇远塔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7][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1《苏州玉田县永济务大天宫寺碑》,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1页。
[8][87]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宝山寺地界记》,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37页。
[9][23][清]张金吾:《金文最》卷67《重修古贤寺弥勒碑》,第978、979页。
[10]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2),《华严寺石柱》,第468页。
[11]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2),《浦公禅师塔记》,第515页。
[12][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中华书局,1986年,第198页。
[13]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龙岩寺碑》,第148页。
[14]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大金泽州松岭禅院记》,第233页。
[15][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1《鄄城县正觉禅院碑》,第1051页。
[16][26][28][30][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0,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054册第682、674、680、682页。
[17][金]李俊民:《庄靖集》卷8《大阳资圣寺记》,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5页。
[18]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施地碑记》,第2647、2648页。
[19][元]脱脱:《金史》卷132《逆臣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19页。
[20][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2《题西庵归一堂》,第34页。
[21]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梵云院碑》,第1334页。
[22]《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张陆村重修功德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9册第298页。
[24]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沁州铜鞮县王可村修建昭庆院记》,第1678页。
[25][清]张金吾:《金文最》卷111《济州普照禅寺照公禅师塔铭》,第1593页。
[27][32][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90页。
[29][元]脱脱:《金史》卷64《后妃传·下》,第1519页。
[31][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纪·下》,第192页。
[33][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3《释氏新闻序》,第277页。
[34]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中都竹林禅寺第十六代清公和尚塔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35][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8《定州创建圆教院碑》,第1134页。
[36]转引自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
[37][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4《平原县淳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第1086页。
[38]《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之2,《大正藏》,第40册第70页下。
[39]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怀州明月山大明禅院记》,第1666页。
[40][元]脱脱:《金史》卷108《侯挚传》,第2388页。
[41][59]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汾州平遥县慈相寺修造记》,第1992页。
[42]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普照禅院牒》,第149页。
[43][49]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3),《金宁国院寿公和尚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58页。
[44]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1),《崇庆院记》,第243页。
[45]王新英:《金代石刻辑校》,《王山十方圆明禅院第二代体公禅师塔铭》,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46]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大金泽州硖石山福严禅院记》,第2046页。
[47]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3),《金大定四年牒》,第188页。
[48][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物产》,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28页。
[50][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22《大正藏》,第23册第743页中-743页下。
[51][宋]陆游撰,杨立英校注:《老学庵笔记》卷6,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03-204页。
[52][53][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第207页。
[54][元]脱脱:《金史》卷92《卢孝俭传》,第2041页。
[55]《辽金寺院遗址最大铸造工场面世》,中国佛教新闻网,www.fixw.net,2011-12-24。
[56]参见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9-270页。
[57][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0《谷山寺碑》,第1035页。
[58]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31《告山赟禅师塔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60]引自林芝:《须弥山石窟史略》,《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61][68][金]元好问:《中州集》卷2《李承旨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68页。
[62]参见李锡厚、白滨著:《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
[63][66][67][元]脱脱:《金史》卷46《食货志·一》,第1033页。
[6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妙行大师行状碑》,第586页。
[69][元]脱脱:《金史》卷96《李晏传》,第2127页。
[70][89][元]脱脱:《金史》卷94《完颜襄传》,第2088页。
[71][76]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奉先县榜》,第45页。
[72][75][清]张金吾:《金文最》卷110《长清灵岩寺妙空禅师塔铭》,第1584页。
[73][88][元]脱脱:《金史》卷47《食货志·二》,第1044、1056页。
[74][元]脱脱:《金史》卷48《食货志·三》,第1073页。
[77]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3),《罗汉院山栏地土公据》,第913-914页。
[78][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1《重修法云寺碑》,第1051页。
[79]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施地碑记》,第2647页。
[80]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大宋河中府中条山万固寺重修碑铭并序》,第1605页。
[81][清]张金吾:《金文最》卷77《灵岩寺田园碑》,第1123、1124页。
[8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49《刘繇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185页。
[83][唐]道宣:《广弘明集》卷24《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1048册第627页。
[84][宋]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1《郑光免税》,中华书局,2002年,第19页。
[85]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9页。
[86]白文固、赵春娥:《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90][清]张金吾:《金文最》卷110《灵岩寺定光禅师塔铭》,第1581页。
参考文献:
①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②林芝:《须弥山石窟史略》[J].《固原师专学报》,1996,(4)。
③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④何兹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⑤白文固、赵春娥:《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农史》2016年第5期)
(编辑:霍群英)